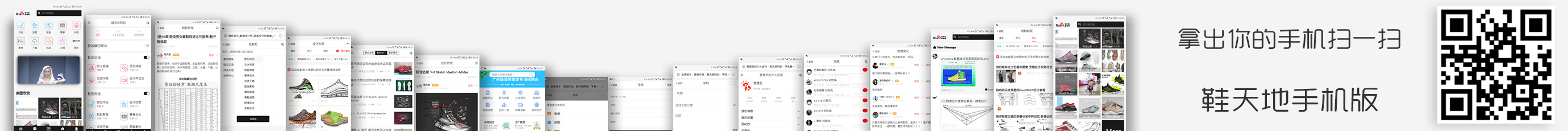|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旅程都有终点或者不终点。我只记得,那一年,我鹄立在某一个陌生站台的傍晚里,夕阳将我的影子弯折在铁轨上,风擦过站台邻近的树梢,扬起我的衣袂和长发。 我静止在那些由两条平行线或无数条平行线组合成的铁轨前,看一列列火车喘着气停在我眼前,又叹着气跑着穿过城市。有什么风正潜入我的耳膜,带着潮湿的夜色和露水的微凉,突然间,满世界只剩陌生,拥挤而荒凉。 我等的那列火车发出阵阵轰鸣,从看不见的深处远方,穿过我的梦幻,叹气着停在我的面前。那激越的声音让我唏嘘回味,含混不清的心有了轻波微澜。 我被人推着送至某一节车厢靠窗的地位,迎面擦肩的,都是不可预期的陌生面貌。我收拾完自己简略的行李,凝视窗外寻思,假想火车奔跑的样子和纷达的方向。 缄默的我不惯与人交谈,在封闭的眼帘背地,我的心奔驰得异样敏捷,铺向远方脉络清楚的铁轨,枯燥地衍生犯错综的迷阵,把人一直送到新的荒漠或热忱的处所,送到也许孤寂兴许喧嚣的远处。而我,想达到的就是那个幸福的站台,实在、温暖。 我晓得,每一趟旅程都由无数的偶尔与不断定形成,我也清楚,同一时间同一列车同一车厢去往统一个地方,已是修了多少世的缘分,但我却难以超越咫尺的间隔,面对陌生我只能无声微笑,随乘坐的火车奔向命定的旅程,却不知一颗曾经带着内伤的心是否在故乡爱情的召唤和不断到来的轰鸣里矗立到地老天荒? 夜已经很深了,只有火车宏大的身躯还在摇摆,无数填充其间的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已入睡,偶然已有一两声细细的低语传动听际。翻看手机上的短信,还浸润着谁从故乡带回的亲情血脉和爱情温度,如听一个人在戗风细语,如被一双温暖的手握着,因为,它装载了太多封闭在胸口的爱和等候。 黑夜里,我睁大眼睛细数时间,我不曾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日子,十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甚至三十过半的此刻,一次次任由火车带我奔向异乡又折回故地。曾经,我安于静止在命定的故乡,认为那样的生活会延长到四平八稳的地步,无惊无扰,然而,我终始站在人群的最边沿,感到如行荒原,荒凉在时间深处,荒凉在黑私下,包含生活与感情。 外面的世界于我并不出色却处处充斥无奈,多年的打拚里,我始终坚持着一滴水的姿势,会在某一天,某一霎时忽然坠落在尘世。城市的繁荣跟喧嚣,从未曾让我忘却本人的来处,生涯的碎片被扔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于是,我想从异乡回到来处,回到分开时的山水和田园里,回到分辨时的友人和情人中。本来,激动和依附已在两地的挂念和等待里静静长成相思。来处,不仅只是时间,还有爱,由于那一份爱始终都在来处守候我,它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面孔提示我一些本源性的事实,让我记取,并暖和我在家乡外面的所有岁月。 于是,彼时此岸,我辗转生疏的站台,以另一种新生的心境从异乡到故乡,运气的迷阵如旷野的风,铺开在面前,披发出琐细浓郁却真实的世间气味,让我眉眼盈盈,不远千里,穿梭旷邈和远征跋涉,在艰巨地绕了一大圈之后,生活又回到原地,我又回到恋情的故乡。 本日,性命在时光的风中一惊,流光把人抛,红颜走失,逝不可追。 当看着一列列火车驶过站台,我会停下来,用全体身心和力气,张望它,设想它当年的样子容貌;感激它,载我来到爱情的站台,直至它从眼前消散。而后宁静的转过身,持续着现世平常而真实的每一天。 |